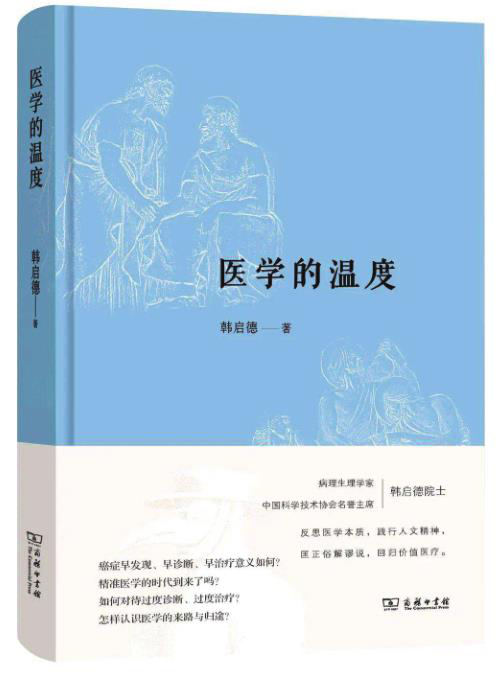
图1 《医学的温度》(商务印书馆,2020年10月)
乍一看书名,许多读者或许会将这本书的主题与内涵局限于就医感受的冷暖与温凉,医患关系的疏离与和谐,不过,这些问题只是表象,韩先生的睿智与深刻在于直击医学的价值与价值的医学。此处绝不是玩文字游戏,韩启德先生书里有两个价值在交争,前者与后者的语义与境界有别、尺度与诉求殊异,前者追求有用、有效、有理的工具理性,后者追求有根、有德、有情、有趣、厚道的价值皈依,可以这么说,前者只是医学的职业价值,而后者则嵌入了人性、人道、人文等人类价值夙愿,意在叩问人类价值光谱中的医学该何去何从。
《医学的温度》篇幅不大,属于大师小书,收入韩先生近年发表的文章20篇,序跋2篇、正文18篇,分三辑,第一辑为主干,有10篇文章,论及医学大趋势及现代性反思;第二辑谈学科嬗变与生死母题;第三辑谈职业主体意识与人文精神追求。
叩问医学的温度,隐含着对诊疗失温的警觉,而失温的背后是人文价值的失焦、失落,工具理性的盛行。可以说,“高冷”是现代医学现代性的标志,真可谓“高处不胜寒”。对此,前辈大师早有洞悉。韩启德先生在书中谆谆告诫人们,应该向历史求答案,医学现代性之谜的探究,医学史不可或缺。联想到他2017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在北大筹建创设科技医史系,并亲自出任首任系主任,新身份的第一场校园公开学术演讲的题目就是《医学是什么:从历史演进看医学的现代困惑》(书中收录了该演讲稿),大有深意。无疑,史学化、人文化、哲学化是许多大科学家晚年的三大觉悟与转型,类同于白石老人艺术风格上的衰年变法,别有洞天,改写了个人的学术轨迹和境界。很显然,韩先生研读历史、书写历史、讲述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忧情,而是借此来透视医学的真谛与现代医学的价值遗缺,更加精准地丈量科学、技术、医学互动中进步的价值风标,洞悉现代医学的来路与前路、初心与皈依。
智者同忧,睿者共识,医学史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曾在《剑桥医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cine)中不无沮丧地抱怨:“人们从来没有活得这么久、活得这么健康,医学从来没有这么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招致人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曾举办一场“现代医学的良知问题”研讨会,会议主席是微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René Dubos),此前,他出版了一部质疑现代医学的专著《健康的幻影:乌托邦、进步和生物学变化》(Mirage de la Santé: Utopies, Progrès, et le changement biologique),会议规模不大,但与会者声名显赫,有牛津大学荣誉内科教授皮克林爵士(Sir G. Pickering)、时任WHO总干事齐索姆斯(B. Chisholms)、美国神经外科学奠基人怀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著名内科学家麦克德莫特(W. Mc Dermott)、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遗传学家赫尔曼·约瑟夫·穆勒(Hermann Joseph Muller)、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基斯佳科夫斯基(G. Kistiakowsky)等科学家,以及《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的作者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和《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作者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人文学者。会议首次发出医学遭遇现代性危机的警讯,缘于医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带来健康乌托邦的幻觉,越来越多的专家认同技术万能、技术决定论,相信技术进步将解决一切人类疾苦问题,甚至逼退衰老与死亡。与会者提醒世人思考理性的医学如何在科学实在与生命存在、技术与人性之间保持张力,让医学真正回归人性,而不是任凭技术主义的惯性去泯灭人类良知。当代医学思想史家詹姆斯·勒·法努(James Le Fanu)在其专著《现代医学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Medicine)中回顾了现代医学的百年飞跃。在他看来,正是科技革命,尤其是大科学、大药业催生了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使得临床医学演化为临床科学,临床医生演变为医学科学家、技术工程师,病人成为受试者,甚至沦为非人化的小白鼠,伴随技术至善主义的抬头,技术至上、观察至上盛行,必然带来医学的去神圣化、去主体化、去情感化,滑向对象化、客体化、数据化。医疗逐渐偏离了救死扶伤的目标,大药业主导诊疗指南与临床路径,检查、处方越来越多,越开越长。于是产生四大悖论:医学做得越多,医生受到质疑和责难越多,医学污名化、医生妖魔化越甚,医患关系越紧张;医疗技术越进步、越精致,健康知识越普及,老百姓误解越多,社会对健康越焦虑,对医疗安全越恐惧,在死亡面前高技术也是无效技术,无法阻挡死神的脚步,只会让濒死的痛苦延长;现代医学越发达,人们对替代医学越热衷;高技术越普及,卫生费用支出及家庭负担越沉重,因病返贫的落差越惨烈,穷生富死越严重。因此,全社会豁达的疾苦观、生死观、医疗观、福利观的确立就显得十分重要。
披览全书,不难发现,韩启德先生并不拘泥,也不满足于先辈的思辨向度、深度与结论,发愿用自己的思想烛火照亮医学发展的来路与前路,为医学反思续写当下的篇章。无疑,现代医学提速增效,犹如驶上高速公路的跑车,各位新老“司机”尤其需要打起精神,紧握方向盘,脚底板在油门踏板与刹车踏板间交替。在韩先生看来,科学是一辆极速赛车,不仅需要改善提速功能,也需要时常检查刹车和倒车性能,就人类价值而言,才是福祉所在。对此,许多科技激进主义者并不认同,他们基于“应然—必然”逻辑行事,仿佛手中有了“榔头”(新技术),满眼都是“钉子”(靶点),都要“敲打”一番。在医学领域,一些任性的“创新”不仅造成患者利益受损,还将导致科技伦理的危机。2018年,基因狂人贺建奎违规从事“基因编辑”就受到了法律与道义的惩处。科学共同体对此类问题也越来越警觉。有鉴于此,韩启德先生在书中再次强烈呼吁:敬畏生命,回归以患者为中心的价值医学。
在韩先生书里,倡导人类价值为先的医学目的、使命,不是高头讲章,而是贴近医学实践的思维导引,认知工具,从这一视角出发,他辩证地审视了癌症“三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理念;深入剖析“中国版”过度诊断、过度治疗的内在根脉、悖论;对当下流行的循证医学、精准医学进行了理性分析;对新兴的叙事医学倾注最大的热忱予以培植、引领;九九归一,他还对生死母题进行了富有哲思的叩问;最后,阐述了“厚道”为皈依的医学职业情怀。
肿瘤的高发、难治、预后不佳,导致“三早”防癌、治癌理念的滥觞,无论普罗大众,还是专业人士,都对此深信不疑。作为病理学家的韩先生却扯起了“反思”的大旗。殊不知,肿瘤是一个大的疾病种类,发生发展的规律并不一致,有陡进型,也有缓进型,还有一些“惰性”癌,也称“懒癌”,如前列腺癌、甲状腺癌,一些中老年的病程延续期甚至超过剩余生命预期,完全可以听之任之,不予理睬,因此,不能一概以“三早”而论治。随着医疗检验技术的长足进步,早发现步入“是癌非癌”的灰色地带,譬如,Pat-CT这类高分辨检测仪器的普及,加之中老年体检频次的加大,许多肺部的“毛玻璃”征象被筛查出来,是继续观察,还是需要立即手术切除?是保守应对,还是激进应对?医患双方都在纠结。癌症普查还带来假阳性病例的涌现,假阳性病例不仅是陪绑者,甚至还因此无端接受了手术与药物治疗,而且“帽子好戴不好摘”,甄别假阳性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专业资源投入,因此,“三早”理念需要因病制宜,因人制宜。不可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强调,否则不仅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还让许多疑似患者受到无端与过度伤害,得不偿失。在中国,过度医疗的滑车许多都是因为“三早”而启动。
医学界一直强调“求真务实”,逻辑实证主义思维主导了临床与科研的全程,凡事拿证据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成为医学界的“铜规铁律”。对此,也要辩证地应对。一方面,医学是人学,有情感、心理、社会因素的投射。疾病不只是仪器的测量结果,而是病人的主观不适;疾病不是非黑即白的客观事实,而是存在诸多灰色地带的人为判读。更重要的是,医疗行为不是客观中立的技术应对,而是包含商业算计的消费行为,医方存在巨大的自由裁量权,由此而言,客观性与主观性,理性与感性,必须保持张力,而不能刻舟求剑,死守规范。书中,韩先生列举了高血压诊疗的认知案例,高血压仅仅只是一个危险因素,不加控制可能造成卒中的危险,但正常血压如何界定?理想血压、标准血压、临床血压,存在着认知差别,一味地追求理想血压,势必造成大规模防治格局的利益化漂移;使用进口药,还是国产药,在防治效果上差别不是很大,但卫生资源利用效率、患者可承受性评估则存在巨大的落差。因此,韩先生劝导我们,要讲证据,但不能唯证据论,要探索中国人口特色的疾病证据体系,继而形成适合中国患者的临床诊疗共识,不可将生命中的危险因素都放大成为疾病,最大限度地凸显“患者为中心”的价值诉求,而决不能被医药利益集团所裹挟。“循证医学不限于技术层面,甚至不限于经济和社会层面,而是关乎医学根本宗旨和目的。”
20世纪医学需要检讨的地方不少,核心是技术之上,使得医学远离人文,医学与社会的隔阂、误解加大,部分医者见病不见人、懂病不懂人、治病不治人,过度医疗愈演愈烈,医学深陷市场魔力场而不拔,医患关系恶质化,究其根本,就是医学初衷的褪色,医学目的的漂移,解决之道是回望初心、回归人文,但这一份回归需要路径,需要思维矫治,韩启德先生敏锐地捕捉到“叙事医学”对医学现代性危机的疗愈价值,于2011年11月4日,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第一次“叙事医学座谈会”,热情地将叙事医学的新理念、新方法推介给中国医学界。无疑,患者来到医院,求助于医生,动因是痛苦的体验,叙事医学创始人丽塔·卡伦(Rita Charon)因而将医学的目的由“救死扶伤”转变为“理解、回应患者的痛苦”,缘于此,医生不仅需要找证据,做决策,还需要听故事、讲故事,在故事里寻找人类苦难的根源,继而共情、反思、建构医患和谐关系,从全人维度帮助患者走出痛苦和疾病,同时,也接纳痛苦与死亡。经过韩启德先生的鼎力推动,如今,叙事医学的幼苗已经育成一片小树林。未来将长成参天大树,探索、创新中国式的“技术—人文双轨诊疗模式”。
精准医学是近年流行于医学界的时髦概念,源自“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先期成果,也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内的两项医学攀登计划(精准医学、脑科学)中的一项。美国在这一项目上投入不大,但后来被推崇为前沿医学的标杆,一些科学家闻风而动,募集大量的资源,拉出一幅决战前沿的态势。对此,韩启德先生头脑很清醒。一方面,生命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存在着永恒的不确定性,如同“芝诺悖论”,医学只能不断逼近精准,而不能抵达终极精准,且在生命境遇中,没有绝对精准,只有相对精准,两者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张力。更重要的是,在当下,基因层面(生物大分子)的探索与系统层面(如脑肠轴、身心交互)、器官层面(多学科协作)、细胞层面(细胞组学、蛋白组学)的探索各有优势,研究的战略布局不应该偏废,厚此薄彼,必然造成医学研究生态的失衡。
价值医学的“引擎”不只在专业技术的修炼,而在“厚道”医风的养成。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创建100周年纪念会上,韩启德先生以“厚道”为题,系统阐述了他的医学教育思想,厚道有两个基点:一是人格锻造,利他、纯粹,有爱心、有责任;二是学术风范的养成,闳阔、深邃,有学养、有见识。人们常常以“桃李芬芳”来形容门下弟子辈出,而在韩先生心中,桃李固然绚烂,却不及胡杨那般坚毅、坚强,它傲然于天地苍穹之间,耐得住风霜与干旱,历千年而不死、不倒、不朽。
韩启德先生很景仰冰心老人,多次在师生聚会的场合朗读冰心老人的一段温馨的散文:“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之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使得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让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挥,也不觉得悲凉。”念到动情之处,他神圣而慈爱的身形定格为一座大山。
通信作者:王一方,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访问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医学哲学、叙事医学。(文章内容来源于《科普创作评论》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