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晚清时期,中国学者李善兰等人编译的《植物学》一书在中国植物学史及中西方科技交流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科技文化影响。该书的编译成功有多种因素,但最关键的是李善兰其汉译的过程中,发挥其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利用创译法完美表达出重要植物学名词的科学含义及文化意味,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传播。
关键词:科技翻译;科学传播;李善兰;《植物学》;晚清时期
由墨海书馆组织翻译并出版的《植物学》(下简称 《植物学》)为晚清第一部植物学方面的译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植物学研究中的基础知识,从而推动了晚清植物学的发展。在该书的合作译介过程中, 李善兰起到了主导作用,尤其是他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的作用,贡献最大。可以说,李氏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及由此形成的创译法,既是译著顺利完成的保障,也是《植物学》后续科学文化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以往关于李氏《植物学》的研究普遍偏重于其科学价值的探讨,而对其以翻译学为基础的中外科技文化交流意义重视不足,更鲜有关注李氏在译介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译者主体性问题。本文从中外科技交流与传播的视角出发,论述李善兰在《植物学》翻译过程中主导作用的发挥,尤其是在植物学名词创译方面的贡献,进而揭示译著《植物学》的科学文化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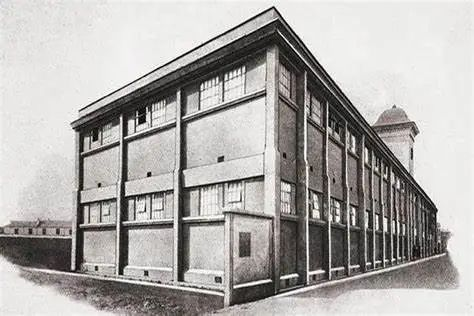
图为墨海书馆
一、李善兰《植物学》译介过程及内容选择
李善兰,为浙江海宁人,是晚清著名数学家,也是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著作翻译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自1852年开始, 李善兰便在科学重镇——墨海书馆开始了其长达8年的译书生涯,所译书籍涵盖了数学、天文、物理、植物学等多个领域,科技翻译成就令人称道,《植物学》即其科技翻译的重要成果之一。《植物学》一书约35000字,插图88幅,其内容材料主要选自英国植物学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 1799—1865)的《植物学基础》(Elements of Botany)及《植物学初步原理纲要》(The Outline 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Botany) 两部书的部分章节。该书译介发生于1858年,发生地为西学重镇——《墨海书馆》,是第二次西学东渐的重要成果之一,能够代表晚清中西方生物学交流的基本状况。
关于《植物学》的译介过程,李善兰在该书“序言”中说:“植物学八卷,前七卷,余(李善兰)与韦君廉臣所译,未卒,韦君因病反(返)国,其第八卷则与艾君约瑟续成之。”就是说,《植物学》的翻译者有3位, 分别为中国学者李善兰(1811—1882)、英国来华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艾约瑟(JosePhEdkins,1823—1905)。译介采取的是 “合译”方式,由中国学者与西方来华传教士合作完成,即由传教士进行口述,中国学者进行笔述。在此过程中,韦廉臣及艾约瑟的主要任务是将原著的英文表达口述成中文,而译语书面表达则由李善兰所敲定。除此以外,李善兰在译介内容的选择及对原著中植物学知识的解读等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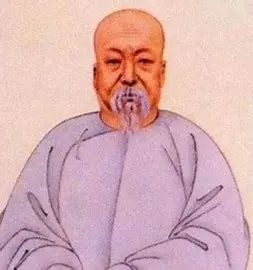
图为李善兰
前已述及,《植物学》一书主要取材于英国植物学约翰·林德利的相关著作,那么,决定待译内容,既是整个翻译工作顺利实施的关键,也是决定译本面貌,实现译本良好效用的前提。李氏虽不懂英文,却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有着全面掌握和深刻理解,这样就保证了汉译内容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促进了汉译成果在中国的传播。
19世纪中期, 墨海书馆的西书汉译进入高潮,大量介绍西方政治、科学和宗教的书籍得以翻译出版,其中包括李善兰《植物学》的译介。值得指出的是,在晚清《植物学》译介发生之前,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长期偏重于实用性,人们对植物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植物本身的药用性及可食用性,研究内容一般被归入农学、中医药学及本草学的范畴,多在相关谱录类著作中得以反映, 植物学并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甚至“植物学”这个名词也是在《植物学》译介之后才问世。而同期的西方植物学研究早已“由表及里”,研究的依据不再是经验主义;植物学研究注重实验观察, 显微镜等科学仪器已得到应用,表达方式也不再是主观的感官描述,研究的侧重点则倾向于植物的内在组织、 细胞等的探索;细胞学说、遗传学说等科学理论已经形成,植物胚胎学、 植物分类学等植物学分支研究初具规模,植物学研究全面发展。因此,晚清时期,中国传统植物学与西方实验植物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差距。
鉴于彼时中西方植物学发展的不均衡性,若将细胞学说、植物学、胚胎学等内容直接引介至晚清科学界, 则可能会超过当时人们的认知范畴,反而不利于近代植物学知识的传播。所以,选定待译内容十分重要,对于译者而言也极具挑战性。与合作者传教士韦廉臣、艾约瑟等人相比,李善兰作为中国学者以及科技翻译家,他更了解晚清中国植物学研究之不足和对西方科学的需求状况, 在选定译本内容时也更有目的性及侧重点, 从而为实现译本的最大效度奠定了基础。具体而言,李善兰等译者所选译的内容并非如遗传学说等较为先进的理论,而是介绍植物体器官功能、植物分类学知识等林德利植物学研究中较为基础性的部分。《植物学》8卷内容中, 前6卷介绍了植物体内部、外部器官的名称及功能,包括内体(聚胞体、乳路体、木体、腺体)、外体(根、干、枝、叶、花、果、种子等),主要向国人介绍植物学内、外体的基础知识,但所选译的内容却并不深奥,且李善兰的译文语言也较为通俗易懂。后2卷介绍的则是植物分类学方面的知识,包括察理之法分部(外长类、内长类、上长类、通长类、寄生类)与分科方面的知识,所介绍的植物分类知识更为细化,其立足点偏重于使用实验解剖学的科学方法。这些知识若从当代植物学研究的视角来看无疑是比较浅显的,但相较于中国传统植物学却是较为新颖的,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植物学与西方植物学的接轨,促进中国植物学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二、植物学术语的创译与表达
李善兰对于外文原本中植物学术语的译介,采取的主要是“创译法”,顾名思义即创造性的翻译。创译法要求译者既需要准确领悟源语中的表意,也需要具备精准贴切的目标语表达能力。他首先对林德利植物学原著中的西方植物学知识进行解读,进而联系晚清中国植物学界乃至整个生物学界的认知状况,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尽量采取传统科学中已有的表述方式。《植物学》一书中恰当贴切的术语翻译,既具备学科专业性又易于为国人所接受,最能体现李善兰创译法的特点和贡献。这些术语包括植物学、细胞、科、心皮、子房、胚、胎座、胚乳、菊科、姜科、雌花、雄花等,它们的翻译首开先河,既规范了中国植物学的术语表达,推动了中国晚清乃至近代植物学的发展,也在科技术语翻译方面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其中李氏创译的“植物学”“细胞”和“子房”三个词最能彰显其译者主体性及创译成果的意义。
在“植物学”一词的译介过程中,李善兰的创译法是如何体现的呢?这要从英文botany被译介为“植物学”的缘起谈起。“植物学”中的“植物”二字并非李善兰所独创,而是他从中国古籍中撷取的。“植物” 一词最早出现于 《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鳞。”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等经典中也曾使用过“植物”一词。古籍中的“植物”一词均是指树木花草类,与动物相对,含义比较明确,李善兰显然深谙其由来和含义。“植物学”中“学”字的确定,则与李氏的译书经历以及晚清科技传播的大背景有关。李善兰在墨海书馆译书期间所接触的人物, 除艾约瑟、韦廉臣等西方传教士外,也包括王韬等中国知名学者。尤其是李、王二人同为书馆译友,过从甚密,在译书及学术上必然有所交集。1855年春,王韬从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口中得知“化学”一词,并记录于自己的日记之中,李善兰有可能从王韬处获得这一学科通名的信息。而且在1858年《植物学》成书之际,地学、天文学、数学等学科名称已经出现,“学”字作为学科通名,与专名组合成为某特定学科的名称,已成为科学界的普遍现象。在英文学科名称botany的翻译过程中,李氏将“学”字置于专名“植物”一词之后,中西合璧,成功创译“植物学”名称。这看似顺理成章,但实际上是其传统文化素养及科技翻译经历的结晶。
从英文“botany”到汉语“植物学”,李氏的翻译简洁明了,传神达意,既尽量保留中国传统的表达方式,又加入了西方的学科概念,影响深远。“植物学”一词问世之后,多部有影响力的植物学著作均沿用了其表达方式,或以其作为译作或著作的题名。如艾约瑟于1886年出版 《植物学启蒙》,会文学社于1903年编译《植物学问答》与《植物学新书》,杜亚泉于1903年编著《新编植物学教科书》,黄明藻于1905年著《应用徙薪植物学》,彭树滋于1906年编写《普通教育植物学教科书》,叶基桢于1907年出版了《植物学》一书。从此,“植物学”被学界不断沿用,逐渐成为统一的学科名称表达。它还包容并统一了传统本草学、区域植物志、植物谱录等名称表达,并促使植物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细胞”一词的译介同样颇有意味。“细胞”译自英文cell一词,并首见于《植物学》一书中。“细胞”的问世,一是李氏研读原作后进行创译的结果,二是受到了译者个人语言习惯(方言)的影响。就前者而言,在林德利原著“论内体”的几卷内容中,对组织构成单位的表达,已有“胞体”的名称。通过对原著中相关植物学知识的研读,李善兰与韦廉臣二人认识到,cell一词指代的是比较小的器官组织构成单位。因此,cell一词被李氏等人先行理解为“小的胞体”,这一表述很贴切但不够简洁。有趣的是,浙江方言这次在英译汉中发挥了作用。李善兰为浙江海宁人,“小”字在其家乡方言中的发音为“细”,于是,“小的胞体”就被翻译为“细胞”。其后虽几经反复,但在20世纪初,“细胞”这一概念表达已被学界普遍认可并采用,一直沿用至今。
还应提及的是,李善兰所创译的植物体器官结构术语,如子房、心皮、胚、胚乳、胚珠等,不仅沿用至今,更为后续的植物显微结构研究及植物生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子房”一词为例,该词的创译是李氏根据植物器官的形状特点及生理功能进行联想, 进而予以形象化表达的结果。子房对应英文为ovary, 为被子植物雌蕊下面膨大的部分,内部包含能够发育成种子的结构——胚珠。其中的“子”字象征了种子,“房”字则既象征了器官的形状,也象征了其功能——为胚珠发育成种子提供处所。可以说,“子房”一词既充分地将对应的器官予以形象化描述,又具备科学术语表达的专业性特征,生动而又贴切简洁。显然,译者如果没有高深的学术造诣和传统文化素养,就不可能做出这些富有灵性的创译成果。
三、《植物学》译著的时代因素及其科学传播意义
李善兰堪称晚清科技翻译第一人,也是走在科学文化前沿的有识之士。他的科技翻译发生在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序幕的“科学救国”思潮之下,因此,《植物学》等科技译著随处反映出切实有效、开启民智的思想,很好地实现了科学传播功能。
《植物学》不仅包括西方植物学的基础性内容,还对其先进成果及注重实验观察的科学研究方法多有推介。在此过程中,李氏能够突破晚清社会科学思想的局限性,较为客观地将西方现代植物学研究成果传播至中国学界及民间。在《植物学》译介发生的19世纪中期,西方植物学研究在生物学整体大发展的带动下,已呈现出体系化特点。遗传学说、林奈“双名制”命名法等生物学理论的提出以及显微镜等实验仪器的应用,标志着西方植物学研究已进入现代意义发展阶段,研究侧重点逐渐偏向于植物解剖学、 植物生理学、植物胚胎学等内容;西方植物学界不断涌现出的名家大师,也为植物学带来了更为先进的理论及方法,促使植物学研究分支趋于细化,研究工作也更为系统化,如1804年索绪尔提出植物光合作用理论,1809年拉马克提出“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法则,以及施莱登、施旺分别于1838年与1839年提出细胞学理论等。然而同期的中国,尚没有专门的植物学学科,植物学研究依然停留在传统博物学范畴,研究内容也跳不出经验性和实用性的窠臼。就是说,与其他自然科学门类相似,晚清时期,西方植物学已远远领先于中国。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中国近代科技全面落后的背景下,清王朝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国人闭目塞听,不愿正视和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很多人拒绝接触西方科技,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文化的进步。在此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故步自封不利于开启民智、振兴国家,他们摆脱狭隘学术思想的束缚,提倡科技救国。于是,晚清以来不少学者试图从介绍和翻译国外科技论著入手,引进和传播西方现代实验科学,以便实现洋为中用的目的,李善兰便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李氏以西方重要植物学文献资料为基础,主持完成《植物学》一书的编译,首次向中国人引介了“植物学”“细胞”等一大批重要科学名词,也描述了植物体在显微镜下的结构呈现及部分生物学原理, 如指出碳是构成生物体的基本物质等。有学者指出,该书“介绍了近代西方在实验观察基础上建立的各种器官组织生理功能的理论,这些理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 可谓是闻所未闻”。这些内容虽然多是现代植物学的基础性知识,但对尚未跨入现代科学门槛的中国人来说,却显得很新颖,具有重要的启蒙价值,并可促使其进一步学习和探索。另外,书中译介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能够引导晚清中国植物学研究与西方接轨, 从而开启中国植物学研究的新时代。尤其是书中创译的大量中文植物学术语表达,为此后的相关论著所广泛采用,部分术语沿用至今,有的还东传日本。总之,在晚清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李善兰的《植物学》译介策略具有显著的开创性和针对性,其翻译成果承前启后,使中国植物学研究迈入新阶段,并为此后西方植物学的进一步传入奠定了基础,从而很好地实现了科学传播功能及文化影响。
李善兰曾说, 自己投身墨海译事有两个目的:一是能接触到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二是能让他衣食无忧,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可见李氏从事科技翻译之目的,虽然不一定那么纯粹,但他在晚清时期能致力于西学汉译事业,以包容的态度接纳西学,以渊博的学识译介西学,的确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植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从而为中国近代科技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植物学》汉译既是晚清植物学界与西方植物学研究接触的重要标志, 也是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发展新阶段的象征。全书篇幅不长,但蕴含的科学文化信息量却极为丰富,既包括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也包括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文化信息,从而为当代学术界考察《植物学》汉译发生时的文化背景、社会信息,挖掘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西方文化因素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植物学》在中国植物学史及晚清中西方交流史上均产生了引人瞩目的影响力,对学术界开展晚清中西方科技交流史研究、传教士科学传教策略研究及晚清科技翻译研究等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结语
晚清时期, 李善兰以创译为核心的翻译策略,保障了《植物学》译介的质量及其后续科学文化影响力的形成。而李氏创译法或译者主体性实现的关键因素,在于其深厚的学养及包容而开放的科学思想,另外也与晚清时期中国植物学发展的需求及墨海书馆西书汉译的环境有密切关系。与此相关,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以及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其他相关科技翻译成果的价值及科学文化传播意义, 也可以从上述角度予以思考和研究。(文章内容来源于林业史,作者系孙雁冰、惠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