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身体有关吗?
这个质疑反映了传统传播研究中存在的盲点。受外部政治、资本权力以及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起源于美国的传播研究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传播的效率问题上,即如何用最短的时间使内容扩散到尽可能大的空间,并取得传播者预想的效果。
传播效率涉及三个维度:空间、时间和同一性。其中,最受重视的是空间和同一性。经验主义传播研究的目标就是提高政治和商业宣传的效果,追求在最短的时间里影响最多的人。这一目标背后的传递隐喻将信息简单等同于物,制造了一个幻象: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可以保真。因此,信息论、控制论及其后继者都致力于克服信息在空间扩散中发生衰减的弊病。
而在追求信息从中心向边缘撒播的过程中,身体自然就变得不受欢迎,因为它限制了信息在空间扩散的幅度。于是,“大众传播”的观念和梦想应运而生——人们希望用技术克服人类肉身的局限,实现信息在远距离空间的及时传递。
除了重视空间,经验研究还重视由传播实现的同一性。同一性是否是传播的首要目标?这个问题暂且按下不论,后文再做探讨。但即便接受了这个前提,经验研究对同一性的理解也比较表面化:它甚至不是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或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主体间性,而是以传者为中心的“效果”,即信息接收者的心理发生传播者期望的改变和服从。受上述对传播同一性理解的影响,身体同样变得无足轻重,甚至可能成为传播的障碍,因为同一性想消除的就是由身体边界导致的人与人的隔绝差异。对经验研究而言,理想的传播就是奥古斯丁所梦想的“没有身体的天使之间的完美交流”。
但是,上述空间和同一性的逻辑在时间维度面前遇到了困难。传者身体的缺席使得“信息可以无衰减地被传递”的幻觉被打破,语境的缺失与传播者之死让人意识到传受双方达成同一性的困难。时间属于人文学者而非通信工程师,前者对文化传承的强调,成为他们对抗后者空间扩张的最后阵地。早在20世纪中叶,加拿大学者伊尼斯(Harold Innis)就发出警告:现代传播技术造成的空间霸权让人们只顾关注从未踏足的远方,却忽略了周遭正在消失的地方文化和传统。恢复身体的功能是伊尼斯开出的药方。他呼吁恢复舌与脚的功能,用身体在场(脚)的口语沟通(舌)抵抗电子媒介,恢复时间维度的文化传承,而不是单纯偏向信息在空间的扩张,重建本地文化——与之相映成趣的是,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人的延伸”则消解了身体与媒介技术的界限,将工具身体化,也将活生生的身体工具化,开创了一条与伊尼斯迥异的通向赛博格的道路。
时间不仅对传播效率提出了挑战,还动摇了原来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空间传递的正当性:如果传播不能跨越时间,是否就能像人们之前想象的那样轻易地征服空间?卡夫卡敏感地意识到,书写文化只是在制造人与幽灵的交流,而非真正的人与人的交流。这也是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中表达的观念:面对面的交流就像真正的爱欲,而书写与演讲这类撒播则像盲目的乱交。身体的不在场也构成了传播的焦虑。
细究起来,传播的同一性问题也不像之前的经验研究认为的那么简单。在经验研究中,对同一性的理解完全是心理主义的。随着对传播认识的深入,“传播效果就是心理反应”开始受到质疑。传播并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说服——这只是站在权力一方的认识,它还是人通过沟通而共同存在的方式,即人与人能否通过传播相互理解、建立共同体。人与人之间为何能够交流?这一行为和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人与外星人、人与物的沟通有何不同?身体的差异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一旦这些问题被打开,身体与传播的关系便不能再被忽视了。
引入身体的视角后,传统传播研究的前提假设中存在的问题就无法回避了。这个前提一方面认为传播是精神交往,与身体无关,并且要在空间上超越身体的限制;另一方面却认为,只有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传播才是理想的传播。这一矛盾暴露出了由于传播研究预设了身心二元论而导致的盲点。仿佛传播只是精神层面的交流,而身体是与此无关、可有可无的,有时甚至还会成为障碍。
但是,要说前人在思考传播问题时完全没有涉及身体,也不公平。身体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若隐若现的话题,一直存在,只不过像“房间里的大象”,被身心二元论一叶障目而已。我们至少可以从比较成熟的研究中整理出四个有关身体与传播的话题:一是现象学的,二是符号互动论的,三是政治经济学的,四是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的。胡塞尔的现象学打开了正视身体问题的大门,提出身体主体、身体是存有的媒介、身体是主体间性(共主观性)的条件等一系列和传播相关的身体命题。首先,胡塞尔注意到身体是感知的媒介,并且活生生的身体并不只是心灵的奴婢,它具有主体性,产生了对空间、节律、逻辑基本原则的感受。这一主题后来被他的忠实诠释者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发扬光大。
其次,因为身体的移动造成了视点变换,才产生了对意向对象的超越。换句话说,我们看到一棵树,并不会只看到树的一面,还会想象树有各个不同的角度,从而获得一个整体的树的形象而不是多棵树的形象。这一对意向对象的超越是身体移动造成的。最后,正是因为拥有相同的身体,我们才能对他人产生第一人称的感受,达成对他者的自我体验(即移情)。因此,身体是构成先验性主体间性的基础。后来,传播学芝加哥学派的米德(George H. Mead)在《心灵、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中把这种站在他人角度、移情的理解视为形成自我、进行人际沟通进而构成社会的前提条件。他的学生库利(Charles Cooley)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镜中我”的概念,认为如果没有对他者的想象与理解,甚至都无法形成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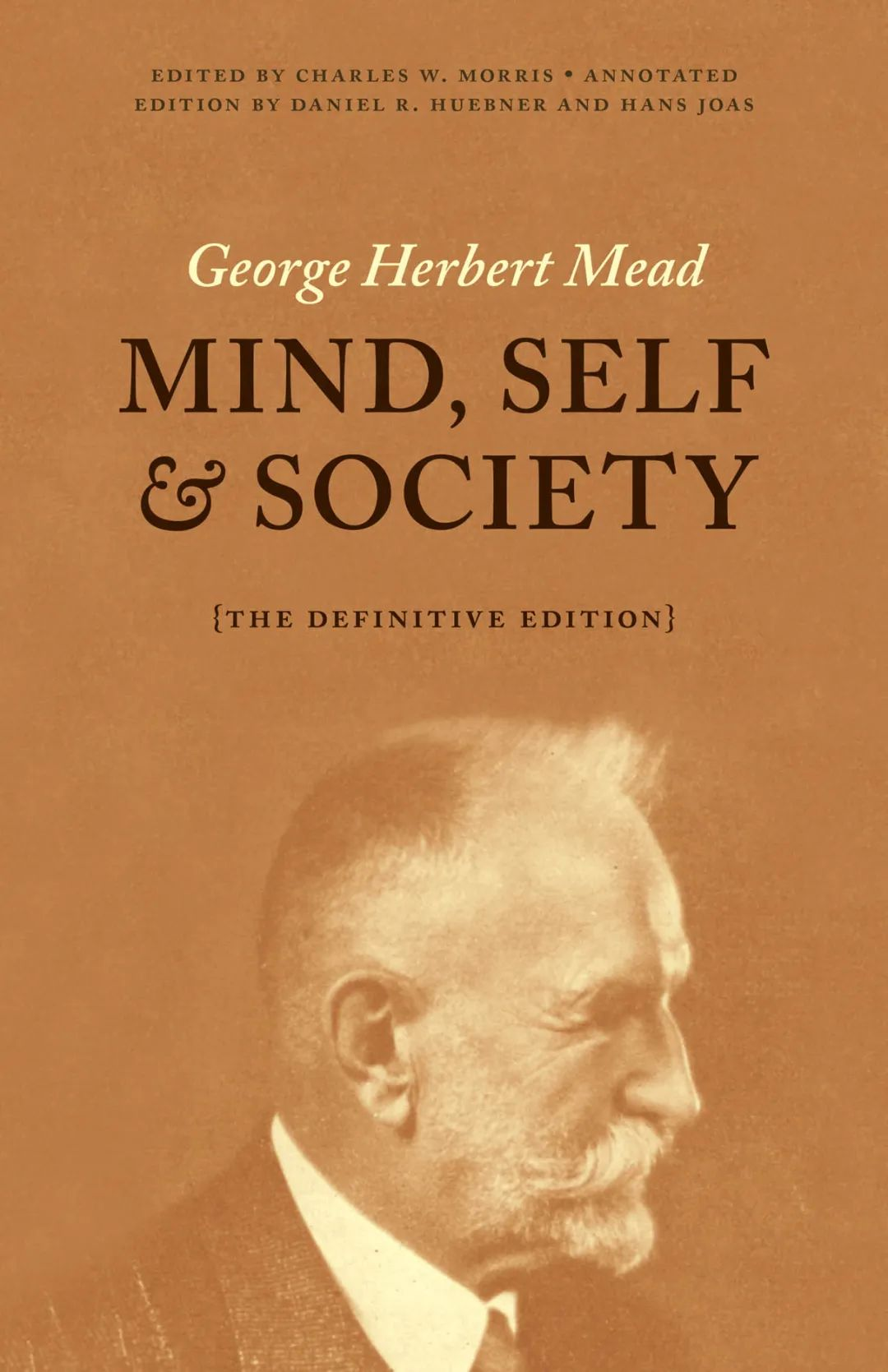
Mind, Self, and Society George Herbert Mea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在胡塞尔的基础上,梅洛-庞蒂进一步提出了身体主体的概念,认为存在一个整体的身体场,它先于且独立于人的理性反思。换句话说,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我感知故我在”——身体成为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最基本的媒介,在思考决定我们是谁之前,感知首先决定着我们如何思考。
除了将身体视为传播的基本前提,传播研究中还有一个更常见的身体概念——作为符号和象征系统的身体。在米德和布鲁默(Herbert Blumer)建立的符号互动理论中,身体的姿态被视为人际互动中的象征符号,人们必须基于对这些姿态的公共意义的理解,才能产生后续行为。这就否定了本能心理学家华生(John B. Watson)等人提出的“刺激-反应”模型,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加上了一个对意义的理解,建立起了“刺激-意义-反应”的新模型。美国微观社会学大师戈夫曼(Erving Goffman)则将这一理论继续发扬光大,他将身体视为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符号系统,认为其中能透露出比言语更丰富、更真实的信息。按照研究跨文化传播的人类学家霍尔(Edward Hall)的说法,这是文化中的“无声的语言”,当身体姿态、编码规则与语境混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复杂的隐性文化。对身体符号编码与意义的讨论是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中的核心话题,身体在其中并没有被忽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身体是主角,在这些领域中,身体自身无法表达,必须被转换成表征和语言之后才能“说话”,所以是“无声的语言”。因此,这还不是真正的传播中的身体问题。
第三个比较成熟的关于身体与传播的话题来自政治经济学。劳动是身体的消耗,因此涉及“传播中的劳动”的话题多少会与身体发生联系。加拿大左派学者斯迈兹(Dallas Smythe)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个盲点,那就是对传播的忽视。斯迈兹提出的“受众商品论”扩展了经典的劳动的概念,认为广播电视受众在免费消费内容的同时,也在付出自己的注意力、身体的紧张与消耗,这和过去身体的劳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广播电视在获得受众的注意力“劳动”后,再将其销售给广告商,从而实现商品的循环。丹 · 席勒(Dan Schiller)则进一步打通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二元对立,把身体的使用与传播隐形的剥削联系在一起。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后来提出的“情感劳动”也是基于身体的损耗。这些理论都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交流中的行为与身体劳动联系在一起,拓展了我们对传播和劳动的理解。
第四个在此前的传播研究中被讨论得较多的话题,是把身体视为文化与权力展开与配置的场所,这也是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中经常涉及的问题。从法国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开始,很多学者便意识到身体并非自然物,而是由文化建构的。虽然身体的生理构造一样,但对其的使用方式却是由文化决定的。因此,当不同文化产生冲突时,身体就成了文化与权力争夺的空间。福柯提出的身体规训、埃利亚斯发现的文明与野蛮在身体上的消长、布尔迪厄所说的惯习、文化研究中发现的亚文化青年通过对身体的另类使用而进行的文化抗争、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体上体现的男性霸权的批判,都体现了这一主题。这些文化与权力如何争夺身体,如何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获得对身体的掌控权,在传播批判理论与文化理论中都比较常见。
在以上四个有关身体与传播的话题中,身体并不是主角,而是扮演着工具或符号的次要角色,人们很少意识到身体与传播密不可分。身体处于传播研究的背景中,它经常是被决定或被影响的因变量、传递影响的中介变量,或者只是一个符号,身体本身一直沉默不语。下面要讨论的五个有待探索的研究主题和上述四个传统话题则有所不同,它们均将身体置于核心位置,从身体的基础性和可供性(affordance)出发,探讨了身体通过传播对人的存在状况产生的影响。(文章选摘自《信睿周报》第61期,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